程序法视角解读最高院156号指导案例
2021-0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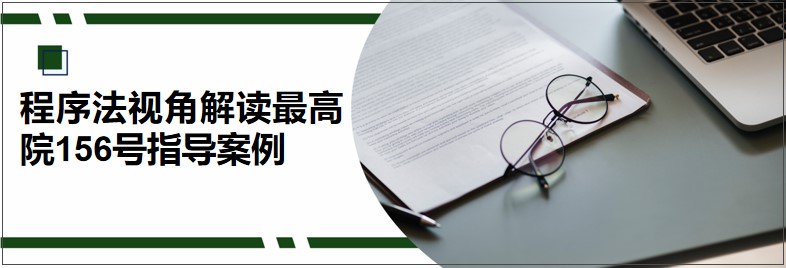
引言:最高院156号指导案例(以下简称“本案”),自2021年3月发布至今已有半年之久。虽然本案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援引和参照,但却鲜有人深究本案所确立裁判规则的确切内涵。与本案相关的既有研究,往往也是仅以本案为引,以实体法视角阐释相关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的内涵[1]。然而实际上,本案的核心并不在于实体方面,而应当在于诉讼请求、竞合合并之诉等程序法问题。基于此,笔者不揣谫陋,试从程序法视角出发解读本案,以求抛砖引玉。
一、最高院156号指导案例概述
2007年,徐意君因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将北京市金陛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陛公司)诉至北京二中院,北京二中院判决解除合同并由金陛公司向徐意君返还预付款。后徐意君向北京二中院申请执行,北京二中院依法查封了金陛公司名下的商品房。
上述商品房被法院查封后,王岩岩得知此事并提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异议。在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王岩岩不服该裁定,向北京二中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北京二中院认为王岩岩之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之规定,故作出(2015)二中民初字第00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得执行该商品房。徐意君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北京高院认为王岩岩之情形不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9条之规定,故作出(2015)高民终字第37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岩岩的一审诉讼请求。王岩岩不服二审判决,以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高法民申254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本案发回重审裁定”),裁定指令北京高院再审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发回重审裁定的裁判理由中指出:《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虽然适用于不同的情形,但是如果被执行人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且被执行的不动产为登记于其名下的商品房,则《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与第29条适用上产生竞合。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选择适用第28条或者第29条规定;案外人主张适用第28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审查。本案一审判决经审理认为王岩岩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规定的情形,具有能够排除执行的权利;而二审判决则认为现有证据难以认定王岩岩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9条的规定,没有审查其是否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9条规定的情形,就直接驳回了王岩岩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上述本案案情系笔者总结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27批指导案例的通知。从本案案情中不难看出,本案的核心问题显然不在于《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第29条的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的确切内涵究竟为何,而是法院在面对可能具有竞合关系的法律规范时应当如何适用法律作出裁判。详言之,既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北京高院二审适用法律错误,那么北京高院究竟为什么错了?法官基于“法官知法”原则似乎应当有适用法律的权力,那么为什么北京高院一定要审查王岩岩之情形是否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以及,本案裁判规则究竟是仅适用于《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还是可以普遍适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笔者接下来将尝试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对本案展开基于我国现行法的理论分析。
二、诉讼请求与处分原则
要解答北京高院在本案二审中为何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还是要从“诉讼请求”这一概念的内涵说起。诉讼请求是《民事诉讼法》中的高频词,但由于我国立法历来追求简略化,《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就诉讼请求这一重要概念的确切内涵予以明示。近些年来,随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这一问题的答案日趋明晰。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其著作中确定的最新观点,在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中(确认之诉的情形较为特殊,本文不赘),诉讼请求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权利主张[2]。这种权利主张所指的权利当然是法定权利,在给付之诉中是请求权,在形成之诉中是形成诉权[3]。亦即,诉讼请求是原告基于特定的权利发生规范(请求权的权利发生规范即请求权基础),请求法院审查其所主张的特定事实能否发生相应法律效果的一种权利主张。
从上述诉讼请求的内涵中不难看出,权利发生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诉讼请求的内容,基于不同权利发生规范提出的诉讼请求也一定是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对诉讼请求内涵的理解,实际上体现了我国法律人士的思维方式[4]。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所谓“规范出发型”的思维方式,即以法律规范中的构成要件为出发点来看待生活中的事实,从而将生活事实转化为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相对应的、对法律适用具备直接意义的要件事实。当然,我国当前民事诉讼中的绝大多数仍为当事人本人诉讼,这是我国的现实国情。因此,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时并非必须指明特定的权利发生规范,而是只要能够通过表明诉讼目的和提出事实主张等方式使法官能够特定化权利发生规范即可[5]。
基于以上铺垫,笔者再来回答本案中北京高院究竟为何必须对《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进行审查,否则即构成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据本案一审判决书记载,王岩岩在一审中提出事实主张:“我已经支付全部房屋价款并实际占有该房屋,对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没有过错[6]。”而结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的规定可以发现,王岩岩主张的“支付全部房屋价款”“占有房屋”“对未办理登记手续没有过错”都是《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之构成要件所对应的要件事实,故王岩岩在一审中当然提出了《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之权利发生规范所对应的诉讼请求。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的处分原则,当事人有权决定民事诉讼的开始、终结和民事诉讼的对象[7]。而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理和判断的对象,指的正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由于权利发生规范本身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一部分,故原告有权选择其请求法院审查的权利发生规范究竟为何。因此,本案中的北京高院在二审中未对王岩岩的情形是否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实际上是未对王岩岩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审理便直接判决驳回,这相当于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当然构成适用法律错误。北京高院之所以犯下错误,还是因为对诉讼请求和处分原则的内涵不甚明了。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改革,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正是以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为核心。因此,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对于我国司法实践还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还需赘述的是,本案的情形实际上更特殊一些。《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虽然属于权利发生规范,但是它们所规定的形成诉权并非通常民事实体法中的形成诉权,而是所谓“程序法上的形成诉权”,即以发生特定程序法上的效果为目的的形成诉权。同样地,虽然一般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属于形成之诉,但此种诉讼也与基于实体法上的形成诉权提起的形成之诉不同,而是被称为“诉讼程序性形成之诉[8]”。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以发生特定程序法上的法律效果为目的,这种法律效果就是部分排除执行根据的执行力。当然,诉讼程序性形成之诉中的诉讼请求确定方式与传统的给付之诉和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并无二致,故本案所确立的裁判规则仍具普适性。
三、权利竞合与竞合合并之诉
前文已述,《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均属权利发生规范,是否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应当遵从原告的选择。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王岩岩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始终未请求法院审查其情形是否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9条。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发回重审裁定中 “《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与第29条在适用上产生竞合”的表述是稍有瑕疵的。
但是,王岩岩能否同时请求法院审查其情形是否符合《执行异议规定》第28条和第29条呢?这就涉及到我国实务中争议极大的权利竞合问题。所谓权利竞合,指的是一个自然的事件,符合不同权利的构成要件,从而产生不同的权利,而这些权利的目的是相同或大致相同的[9]。从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并没有任何法律或者理论限制王岩岩以如此的方式起诉。王岩岩倘若如此起诉,实际上是并列提出了两个诉讼请求(虽然形式上通常表现为一个诉讼请求),而这两个诉讼请求都具有部分排除执行根据执行力这一相同目的。但是在另一种更广为法律人士熟知的权利竞合情形,即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竞合的情形下,《民法典》第186条(及原《合同法》第122条)却要求原告对这两种请求权择一行使。
实际上,上述两种情形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允许权利人同时提出相互竞合的权利主张,有助于权利人的权益保护和纷的一次性解决,但对法官的裁判技术要求较高[10]。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妥善解决权利竞合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法》中的诉之合并制度,明确允许原告提起竞合合并之诉。竞合合并之诉指的是在权利竞合的情形下,原告基于同一诉讼目的,在同一诉讼中提出相互竞合的多个权利主张的诉讼模式[11]。依照我国对于诉讼请求内涵的理解,竞合合并之诉中存在多个诉讼请求,法官也应当对这多个诉讼请求都作出裁判。同时,由于相互竞合的数个权利所对应的权利发生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仍有区别,故原告可以对数个诉讼请求排序,请求法官依次审查。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应当关注相竞合的数个权利在消灭上的牵连性,至多支持原告提出的一个诉讼请求,并对所有诉讼请求作出裁判。
当然,我国当前尚不能完全接受竞合合并之诉本身不属于十分严重的问题,这通常仅会导致当事人的讼累以及对原告期限利益的侵害。但是,我国有部分法官曲解《民法典》第186条的规定[12],认为当事人在首次选择提出某一权利主张并败诉后,也不能再依据另一权利发生规范另行起诉。这种错误的观点非但不符合《民法典》第186条的立法原意,更是直接导致原告的权利根本无法实现。具体而言:首先,这种观点从程序上不受理原告提起的后诉没有依据,因为原告提起的前后两诉系基于不同权利发生规范,两个诉讼请求既不相同又不存在任何先决关系。其次,这种观点相当于要求原告在首次选择是必须精准地选取权利发生规范,否则即承受全面失权之不利后果,这显然对于原告过于严苛。最后,这种观点与《民法典》第186条所追求的赋予原告选择权,充分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立法理念背道而驰,反而是为作为被害人的原告挖下了一个“法律陷阱[13]”。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法》虽然当前没有对竞合合并之诉作出明确规定,但原告通常是可以提起竞合合并之诉的。《民法典》186条对于原告不可同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应属例外规则,但法律人士应当准确理解该条的内涵。
结语
与实体法相比,程序法总是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即使是法律专业人士,也往往更热衷于以纯粹的实体法视角探究法律规范适用的妥当性和正确性[14],而不愿深究程序法问题。但必须承认的是,程序法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程序法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甚至决定了实体法的实然效力。近年来,我国民事程序法高速发展。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是在2022年,《民事诉讼法》又将迎来五年一度的大修,《民事强制执行法》也将作为一部独立的程序法法典出台。新时代的法律专业人士,应当具备以程序法视角看待问题,以程序法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仅尝试以最高院156号指导案例为素材,从程序法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判观点展开分析。
限于笔者水平,文中必有诸多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参见:李崇文、吴坤、陆迪:《基于156号指导案例发布,聚焦不动产买受人排除强制执行要件认定》,载“中伦视界”微信公众号,2021年4月15日发布;王欣欣:《案例评析(156号指导案例):房屋买受人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载“立方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2021年4月16日发布等。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498页。
[3]参见严仁群:《诉讼标的之本土路径》,载《法学研究》2013年03期。
[4]参见沈德咏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634-635页。
[5]参见任重:《论我国民事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21年02期。
[6]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初字第00461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载《法学评论》2000年04期。
[8]参见杨与龄著:《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1页。
[9]参见段厚省:《请求权竞合研究》,载《法学评论》2005年02期。
[10]参见叶名怡:《<合同法>第122条(责任竞合)评注》,载《法学家》2019年02期。
[11]参见李龙:《民事诉讼诉的合并问题探讨》,载《现代法学》2005年02期。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439号民事裁定书。
[13]参见王德新:《<民法典>中请求权竞合条款实施研究》,载《法学杂志》2021年05期。
[14]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载《法商研究》2016年02期。
本文作者:

指导合伙人: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